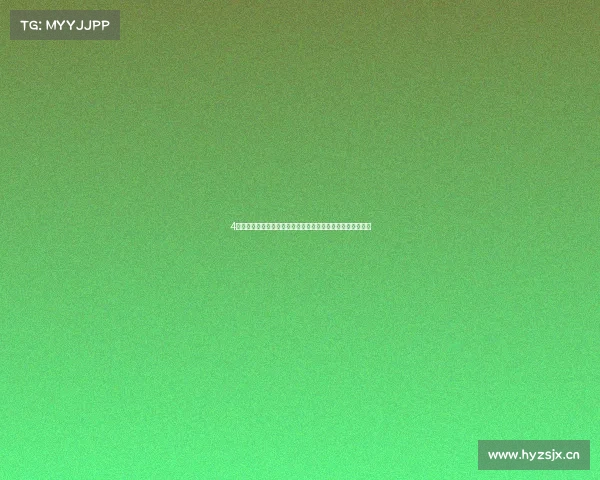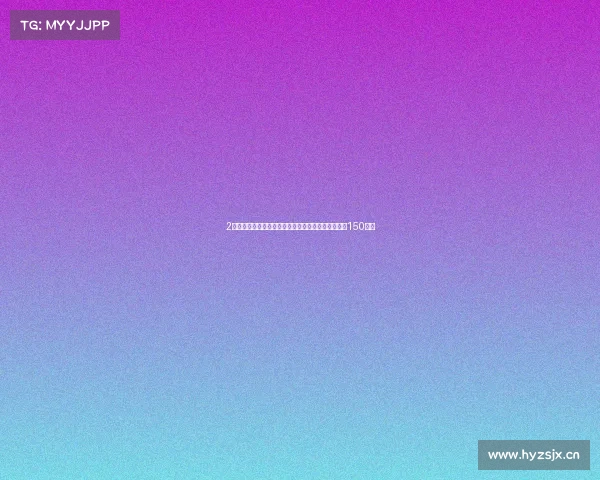90年他花200买下潘家园破碗,摊主嘲他眼瞎,拍卖成交价让他泪目
一
1990年的秋天,北京的风已经有了凉意,卷着半黄不黄的叶子,在胡同里打着旋儿。
我叫林卫东,那年三十五,不大不小的年纪,却卡在一个尴尬的人生当口。
——我下岗了。
从红火了二十多年的国营机床厂出来,手里捏着那点微薄的买断工龄钱,心里跟那秋风里的落叶一样,没着没落的。
老婆秀兰倒是没多说啥,就是叹气的次数多了,做饭的时候,以前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交响曲,现在也变得悄无声息。
我知道她愁。
儿子刚上初中,哪哪儿都要钱。
我一个大男人,总不能在家吃现成的。
朋友给介绍了几个活儿,去工地扛水泥,去饭馆当保安,我心里都过不去那道坎。我林卫东,好歹也是厂里拿过技术标兵的八级钳工,这双手是跟精密仪器打交道的,怎么能去干那个?
心里憋着一股劲儿,没处使。
唯一的念想,就是去潘家园转转。
这毛病是跟我爸学的。老爷子以前是琉璃厂的学徒,解放后进了单位,一辈子就好个瓶瓶罐罐。我从小耳濡目染,虽没学到他老人家的真传,但眼力劲儿,自认比一般人强点。
以前兜里有俩闲钱,周末就爱往那儿扎。
现在,是真不敢了。
可脚底下跟有自己的想法似的,蹬上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,晃晃悠悠就奔着潘家园去了。
那天是个周末,潘家园里人挤人,跟赶大集似的。
空气里混着泥土味儿、汗味儿,还有各种老物件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陈旧气息。
我推着车,在人堆里慢慢地蹭。
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吆喝声、砍价声。
“嘿,哥们儿,看看这鼻烟壶,正经的内画!张口就出价,给钱就拿走!”
“大姐,您再瞧瞧这玉镯子,水头足着呢!给您老母亲戴,保准显年轻!”
我就是个看客,纯粹的。
兜里那二百块钱,是秀兰给我这周的生活费,说好了要去副食店给儿子买两斤肉,改善改善伙食的。
我攥了攥口袋,心里告诫自己,饱饱眼福就行,可千万别动心思。
二
人就是这样,越是告诫自己别干什么,那事儿就越是往你眼皮子底下凑。
我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停住了脚。
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瘦猴,穿着件褪了色的蓝布褂子,脸上沟壑纵横,一双眼睛贼亮,透着精明。
人称“马三儿”。
潘家园的老油子了,真真假假的东西在他那一掺和,能把新手侃晕。
我本来是想绕过去的,眼神却不经意地扫过他地摊的角落。
那儿,孤零零地摆着一个碗。
一个破碗。
碗沿上磕了老大一个口子,还带着几条细细的冲线,像是被人从土里刨出来,又随手扔在那儿的。
碗身上沾满了黑乎乎的泥垢,几乎看不出本来的颜色。
就是这么个玩意儿,却像块磁铁,把我死死吸住了。
我蹲下身子。
心,没来由地跳了一下。
一下,又一下,跟擂鼓似的。
我爸说过,老物件是有“气场”的。有的霸道,有的温润,有的杀气腾腾。
这个破碗,给我的感觉,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“静”。
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儿,周围的喧嚣、嘈杂,似乎都跟它没关系。它自成一个世界,一个沉淀了无数时光的世界。
我伸出手,想去摸摸。
“嘿,我说哥们儿。”
马三儿的声音跟淬了油似的,又尖又滑。
“看上嘛了?我这儿的东西,保真!您瞧瞧这唐三彩的马,这品相!”
他指着摊位正中间一个鲜亮得有些扎眼的陶马,唾沫横飞。
我没理他,眼睛还盯着那个碗。
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捧了起来。
很轻。
入手的感觉,温润,细腻,完全不像普通的粗瓷。隔着厚厚的泥垢,我仿佛能摸到它骨子里的那种质感。
我把碗翻过来,想看看底足。
底足也糊满了泥,但隐约能看到修足的工艺,利落,干净,没有一丝拖泥带-水。
我的手,开始微微发抖。
这不是激动,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理反应。
我爸说过,真正的好东西,是能跟你的血脉产生共鸣的。
“我说,你相中那个破碗了?”
马三儿凑了过来,脸上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嘲弄。
“那玩意儿是我乡下收货搭来的,就一破烂儿,你要是喜欢,搭个十块八块的,拿走当个烟灰缸得了。”
周围有几个看热闹的,也跟着嘿嘿笑了起来。
“老林,你这眼神不行啊,放着这么多好东西不看,看上个破碗?”
说话的是个熟脸,也是常在潘家园晃荡的“串儿”。
我没说话。
我用大拇指的指甲,在碗底轻轻地刮了一下。
泥垢脱落,露出了一小片釉面。
那釉色……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
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颜色。
天青色。
但又不是简单的天青色。
釉色里透着淡淡的微光,像是雨后初晴的天空,干净,纯粹,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静谧。
“雨过天青云破处,这般颜色做将来。”
我爸当年教我背这句诗的时候,眼睛里放着光。他说,这是古人形容柴窑的。
柴窑。
那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,五代后周柴世宗的御用瓷器。
“薄如纸,明如镜,声如磬”。
传说中的“瓷皇”。
我的呼吸,一下子就停住了。
不可能。
绝对不可能。
柴窑存世稀少,据说全世界加起来,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别说一个破碗,就是一个碎片,那都是国宝级的。
怎么可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扔在一个地摊上?
我一定是疯了。
下岗把脑子下出毛病来了。
我对自己说。
三
我把碗放下了。
站起身,准备走。
理智告诉我,这绝对是个圈套。马三儿这种人,精得跟猴儿似的,他会不认识好东西?这八成是他做的一个局,专门等着我这种一知半解又爱做梦的棒槌往里钻。
我迈开腿。
可那碗的影子,却跟长了脚似的,在我脑子里来回地晃。
那片天青色,像一根针,扎在我心尖上。
万一呢?
人这一辈子,能有几次“万一”?
我爸玩了一辈子古董,到老了,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手“捡”着一个大漏。他总说,这行当,靠的是眼力,但有时候,更靠的是胆量和缘分。
东西跟你有没有缘,就看那一瞬间,你敢不敢出手。
我停住了脚步。
身后,马三儿的吆喝声还在继续,夹杂着旁边人的哄笑。
“那哥们儿,估计是让那破碗给镇住了,哈哈哈!”
“八成是没钱,过过手瘾。”
这些话,像一根根小刺,扎得我后背生疼。
我猛地转过身。
重新蹲下,再次把那个碗捧在手里。
这一次,我看得更仔细。
碗的口沿虽然破了,但能看出器型的规整。是一种很微妙的弧度,多一分则肥,少一分则瘦。
我用指关节,轻轻地叩了一下碗身。
“铛——”
声音清脆,悠长,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回响。
如磬之声。
我的心,又一次被攥紧了。
“我说哥们儿,你到底要不要啊?”马三儿有些不耐烦了,“别在这儿耽误我做生意。”
我抬起头,看着他。
“这碗,怎么卖?”
马三儿愣了一下,随即脸上堆满了夸张的笑容,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
“哟,还真看上了?行啊,有眼光!”他竖起一个大拇指,但那眼神里的轻蔑,谁都看得出来,“我刚才说了,十块八块的……”
他话还没说完,我就打断了他。
“我正经问你,开个实价。”
我的声音不大,但很坚定。
马三-三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,那眼神像是在评估一件货物的价值。
他可能看出了我身上的寒酸,但也看出了我眼神里的那股子执拗。
他眼珠子一转,计上心来。
“行,看您是真心喜欢。”他清了清嗓子,伸出两个手指头,“这个数。”
“二十?”
“二百!”
马三儿的声音陡然拔高,生怕周围的人听不见。
“二百块,买个破碗?”
“马三儿,你可真敢要啊!”
“这不欺负人嘛!”
周围的人又炸了锅。
九十年代的二百块钱,不是个小数目。一个普通工人,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。
秀兰给我的,正好二百。
那是我们家一个星期的菜钱,是儿子的书本费。
我攥着口袋里的钱,手心全是汗。
那钱,仿佛有千斤重。
“怎么,嫌贵?”马三儿抱着胳膊,斜眼看我,“我跟您说,这玩意儿看着破,说不定是宋朝的呢!二百块买个宋代民窑,您上哪儿找这好事去?”
他嘴上说着宋代,但那语气,分明就是在说“这就是个破烂,我就是讹你,你能怎么着”。
他在激我。
他在赌。
赌我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心,赌我下不来台。
我看着他,他也看着我。
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我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。
一个说,林卫东,你疯了!快走!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,你要把老婆孩子都搭进去吗?
另一个说,林卫东,你这辈子就甘心这么窝囊下去了吗?这是个机会,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!
我爸的脸,秀兰的脸,儿子的脸,在我眼前来回切换。
最后,定格在那片雨过天青的釉色上。
我深吸一口气。
从口袋里,掏出了那二百块钱。
钱有些旧,带着我的体温。
我一张一张地数,数得很慢。
“给你。”
我把钱递给马三-三。
整个世界,在那一瞬间,都安静了。
马三儿脸上的表情,从错愕,到狂喜,最后变成了一种近乎怜悯的嘲讽。
他飞快地把钱从我手里抽走,塞进怀里,动作麻利得像个变戏法的。
“得嘞!您敞亮!”
他把那个破碗往我手里一塞,生怕我反悔。
“哥们儿,您这眼力,绝了!”他冲着周围的人嚷嚷,“今天我马三儿算是开了眼了,二百块买个破碗,这位爷,是真玩家!”
周围传来一阵哄堂大笑。
那笑声,像无数只手,在撕扯我的脸皮。
火辣辣的疼。
我没说话,用我那件旧的确良衬衫,小心翼翼地把碗包好,揣进怀里。
我能感觉到它隔着布料传来的温润。
我推起车,在众人的指指点点和嘲笑声中,逃也似的离开了潘家园。
身后,马三儿那刺耳的声音还在飘荡。
“又一个眼瞎心盲的,哈哈哈……”
四
回家的路,我骑得特别慢。
秋风吹在脸上,凉飕飕的。
可我的心,却是滚烫的。
怀里的那个碗,像一团火。
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到底对不对。
理智上,我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。
可情感上,却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期待。
就像一个赌徒,押上了全部身家,在等待开牌的那一刻。
回到家,天已经擦黑了。
一进门,就闻到一股棒子面粥的香味。
秀兰在厨房里忙活,听到我开门,头也没回地说:“回来了?今天厂里有消息没?”
她还在盼着厂子能回心转意,把我给要回去。
“没。”
我低低地应了一声,换了鞋,想溜进自己那间小屋。
“站住。”
秀兰的声音从厨房传来,带着一丝严厉。
我停住了脚步,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
她从厨房出来,手里还拿着锅铲,身上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。
“我让你去买的肉呢?”
她看着我空空如也的双手,眉头皱了起来。
“我……”
我张了张嘴,却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“钱呢?”她的声音又冷了几分。
我喉咙发干,半天说不出话。
秀兰的目光,落在了我鼓鼓囊囊的怀里。
“你揣着什么呢?”
她走过来,一把就掀开了我的衬衫。
那个用旧衣服包着的碗,骨碌一下,滚了出来。
幸亏我眼疾手快,一把捞住了。
秀兰愣住了。
她看着我手里的那个破碗,又看看我,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。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?”
“一个碗。”我小声说。
“碗?”她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,“你拿我给你的二百块钱,就买了这么个……破玩意儿?”
她的声音开始发抖。
“秀兰,你听我解释……”
“解释什么?林卫东,你长本事了啊!”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碗,举到我面前,“你看看!你给我好好看看!这上面一个大豁口!这能叫碗吗?这连要饭的都嫌磕碜!”
“你花二百块,就买了这么个东西?!”
pc28预测“二百块!你知道二百块能买多少斤肉吗?能给咱儿子买多少本练习册吗?那是咱们家一个星期的命!”
她的眼圈,一下子就红了。
“你下岗了,我不怪你。你在家待着,我一个人上班养着你,我也不怪你。可你不能这么作践这个家啊!林卫东,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好欺负了?”
她说着,举起手里的碗,就要往地上摔。
“别!”
我吓得魂飞魄散,一个箭步冲上去,死死抓住了她的手腕。
“秀兰!你听我说!这碗不一样!”
“有什么不一样?不就是个破碗吗?!”
“它可能是柴窑!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“柴窑?”秀兰愣了一下,随即冷笑起来,“林卫东,你是不是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看魔怔了?还柴窑?你怎么不说它是金饭碗呢?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,跟那些走火入魔的赌徒有什么区别?”
“我没疯!”我急得满头大汗,“爸教过我的,你忘了?这釉色,这声音,这质感……错不了的!”
“你爸?你爸玩了一辈子,连个响儿都没听见!你就跟他学了几天,就敢自称专家了?”秀兰的话,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,“林卫东,我告诉你,今天这事儿没完!你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,这日子,没法过了!”
她说完,把碗往桌子上一扔,转身进了卧室,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我看着桌子上的碗,又看看紧闭的房门,心里一片冰凉。
儿子从他的房间里探出个小脑袋,怯生生地看着我。
“爸……”
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
“没事儿,写作业去吧。”
整个晚上,秀兰都没再出来。
我一个人,就着一盘咸菜,喝了两碗棒子面粥。
粥是凉的,心,也是凉的。
夜深了,我把那个碗拿回自己的小屋,用清水,一点一点地把它清洗干净。
泥垢褪去,它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
在昏黄的灯光下,那碗身通体呈现出一种温润如玉的天青色,釉面光滑,开着细密的片纹。
那个豁口,虽然刺眼,却无法掩盖它本身那种高贵而静谧的气质。
我看着它,入了迷。
这一夜,我没合眼。
我守着这个碗,就像守着一个摇摇欲坠的梦。
五
第二天,我起了个大早。
秀兰已经上班去了,桌上给我留了早饭,一个窝头,一碗粥。
还是冷的。
我知道,她还在生气。
我必须得做点什么,证明我不是个疯子。
我第一个想到的人,是范叔。
范叔叫范志远,是我爸生前最好的朋友,也是琉璃厂退下来的老师傅,在古玩行里,是泰斗级的人物。
老爷子眼力毒辣,为人又正派,轻易不给别人掌眼。但他跟我爸的交情,比亲兄弟还亲。
我小心翼翼地把碗用好几层软布包好,放进一个布兜里,挂在胸前。
然后蹬上我的二八大杠,直奔范叔家。
范叔家住在后海的一个小院里,院子里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,收拾得干净利落。
我到的时候,范叔正戴着老花镜,在院里的石桌上看报纸。
“范叔。”我怯生生地喊了一声。
范叔抬起头,看到是我,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。
“是卫东啊,快进来坐。有日子没见了,最近怎么样?”
“还……还行。”我支支吾吾地说。
“别跟我来这套虚的。”范叔摘下眼镜,指了指对面的石凳,“坐。我听说了,厂子里的事,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凭你的手艺,到哪儿都饿不着。”
范叔的话,让我心里一暖。
“范叔,我今天来,是想请您……帮我瞧个东西。”
我一边说,一边紧张地从怀里掏出那个层层包裹的碗。
范叔的表情,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。
他知道这行当的规矩,也知道我爸的脾气。不是碰上自己吃不准的“大货”,我是绝对不会来麻烦他的。
他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我把碗放到石桌上,一层一层地揭开包裹的软布。
当那个天青色的破碗,完整地出现在范叔面前时,他的眉头,微微地皱了一下。
他拿起碗,没有先看釉色和器型,而是直接翻到了碗底。
他的手指,在碗底那个模糊的刻款上,轻轻地摩挲着。
时间,一分一秒地过去。
院子里静悄悄的,只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
我的心,提到了嗓子眼。
过了足足有五分钟,范叔才缓缓地抬起头,看着我。
他的眼神,很复杂。
有惊讶,有疑惑,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。
“卫东,这东西……你从哪儿得来的?”
他的声音,有些沙哑。
我把昨天在潘家园的经历,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。从看到这个碗的第一眼,到跟马三儿的交易,再到回家跟秀兰吵架,没有丝毫隐瞒。
范叔静静地听着,没有插话。
等我说完,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“二百块……你这小子,胆子可真不小啊。”
他顿了顿,又把目光投向了那个碗。
“你爸要是还在,看到这东西,估计得高兴得三天睡不着觉。”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“范叔,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范叔没有直接回答我,而是从屋里拿出了一个高倍放大镜。
他对着碗身上的釉面,仔仔细-细地看了起来。
“你看这釉里的气泡。”他指给我看,“大小不一,疏朗有致,像是天上的星星。这叫‘寥若晨星’。这是柴窑一个很重要的特征。”
他又指着碗底。
“再看这底足,‘裹足支烧,芝麻挣钉’。虽然泥垢还没完全清理干净,但痕迹还在。”
他放下放大镜,闭上眼睛,像是在回味什么。
“我年轻的时候,有幸在故宫的库房里,见过一次公认的柴窑残片。那感觉,那神韵……”
他睁开眼,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
“卫东,如果我没看错的话,你小子……这次是真的要捅破天了。”
“这……这真是柴窑?”
我的声音,抖得不成样子。
“八九不离十。”范叔的语气,斩钉截铁,“虽然它破了,但它的价值,也远不是你那二百块钱能衡量的。”
“那……那它值多少钱?”我傻傻地问。
范-叔笑了。
“值多少钱?卫东,这东西,不能用钱来衡量。它是咱们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座丰碑,是无数陶瓷工匠的终极梦想。”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语重心长地说:“不过,既然到了你手里,就是你的缘分。这东西,你自己可藏不住。怀璧其罪的道理,你懂吗?”
我点了点头。
“范叔,那我该怎么办?”
“两条路。”范叔伸出两个手指,“一条,是直接捐给国家。故宫博物院,或者国家博物馆,他们会给你发一张奖状,或许还有几千块钱的奖金。你林卫东的名字,会跟着这个碗,一起被记入史册。”
“另一条路呢?”
“另一条路,”范叔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,“就是找一个最顶级的拍卖行,把它推向市场。让全世界的收藏家,都来看看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,到底有多厉害。”
“这条路,能让你彻底翻身。你下岗的这点事,以后在你的人生里,连个屁都算不上。”
“但是,”他话锋一转,“这条路,也凶险。人心叵测,一旦消息泄露出去,你可能会有天大的麻烦。”
我沉默了。
捐给国家,名垂青史。这是我爸那一代人的理想。
可是,我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开了胶的旧皮鞋,想着秀兰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,想着儿子那渴望一双新球鞋的眼神……
我需要钱。
我需要让我的家人,过上好日子。
我需要证明给所有人看,我林卫东,不是一个废物。
“范叔,”我抬起头,目光坚定,“我想走第二条路。”
范叔看着我,良久,点了点头。
“好,有志气。”
“这件事,我来帮你联系。你在京城,人生地不熟,容易被人坑了。”
“不过,卫东,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范叔您说。”
“不管这碗最后拍出多少钱,你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。不能忘了,你是一个手艺人,是一个钳工。钱,能改变你的生活,但不能改变你的心。”
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“范叔,我记住了。”
六
从范叔家出来,我感觉自己像是踩在云彩上,轻飘飘的,不真实。
天,还是那个天。
街,还是那条街。
可我的世界,好像已经不一样了。
回到家,秀兰还没下班。
我破天荒地走进厨房,把昨天剩下的棒子面粥热了,又炒了两个家里仅有的鸡蛋。
等秀-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,看到桌上的饭菜,愣住了。
“你……这是干嘛?”
“吃饭吧。”我给她盛了一碗粥。
她没动,就那么看着我。
“林卫东,你别跟我来这套。那个碗的事,你要是不说清楚,这饭我吃不下去。”
我放下筷子,看着她的眼睛。
“秀兰,我今天去找范叔了。”
听到“范叔”两个字,秀兰的表情缓和了一些。她知道范叔在我心里的分量,也知道范叔的为人。
“范叔怎么说?”
“范叔说,”我顿了顿,一字一句地说,“那碗,是真的。”
“真的?”
“真的。”
“那……值多少钱?”她小心翼翼地问。
“范叔说,不好估价。但他说,这东西,能让我彻底翻身。”
秀兰的嘴唇,哆嗦了一下。
她没再说话,默默地端起碗,开始喝粥。
喝着喝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一颗,一颗,砸在碗里。
我知道,她这些天,受了太多的委屈。
我伸出手,握住了她的手。
她的手很粗糙,都是干活磨出来的茧子。
“秀兰,对不起,让你跟着我受苦了。”
她摇了摇头,哽咽着说:“只要……只要你是对的,就行。”
那天晚上,我们聊了很久。
我把范叔的话,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。
当听到“柴窑”两个字的时候,她虽然不懂,但从我的语气里,她能感受到那两个字的分量。
当听到可能会有天价的时候,她的眼睛里,第一次露出了光。
那是一种对未来的,充满希望的光。
“卫东,那……咱们真的要发财了?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摇了摇头,“但至少,有希望了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,变得既漫长,又充满了期待。
范叔帮我联系了国内最顶尖的一家拍卖行,叫“华夏拍卖”。
对方听说疑似柴窑现世,高度重视,派了一个姓陈的资深专家,亲自上门拜访。
见面的地点,就约在范叔家。
那天,我跟秀兰都去了。
我们俩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。我穿上了那件压箱底的蓝色中山装,秀兰穿上了她结婚时做的那件红色的确良连衣裙。
陈专家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戴着金丝眼镜,文质彬彬,说话不急不缓。
他看到那个碗的时候,反应跟范叔差不多。
也是先皱眉,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和观察。
他带来的工具,比范叔的更专业。除了放大镜,还有各种光源和检测仪器。
他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。
最后,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,摘下眼镜,用一块丝绸手帕,仔细地擦了擦。
“范老,林先生。”
他站起身,对着我们,微微鞠了一躬。
“我以我二十年的从业经验担保,这件天青釉撇口碗,是五代后周柴窑真品,无疑。”
“虽然口沿有残,但瑕不掩瑜。它的出现,足以填补我们国家陶瓷史的一项空白。”
“我们华夏拍卖,非常荣幸,能够代理这件国之重宝的拍卖事宜。”
我的脑子,一片空白。
秀兰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,指甲都快掐进我肉里了。
我能感觉到,她在发抖。
我也在发抖。
“陈……陈专家,”我结结巴巴地问,“那……您看这件东西,大概能……能拍到多少?”
陈专家笑了笑,重新戴上眼镜。
“林先生,柴窑无价。这是收藏界的共识。”
“不过,非要给它定一个市场价的话……我只能给您一个保守的估价。”
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。
我跟秀-兰对视了一眼。
“一……一万?”秀兰试探着问。
陈专家摇了摇头。
“十万?”我壮着胆子猜。
陈专家还是摇了摇头。
他看着我们,缓缓地说道:“起拍价,一百万。”
“至于最终能成交到多少,就要看市场的反应了。但我个人估计,打破国内单件瓷器的拍卖纪录,应该不成问题。”
一百万。
一百万!
我跟秀兰,都傻了。
我们俩,这辈子见过最多的钱,就是我下岗时拿到的那几千块买断费。
一百万,对我们来说,是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。
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。
一个荒诞的,却又无比真实的梦。
七
签完委托拍卖合同,我和秀兰浑浑噩噩地走出了范叔家。
北京的阳光,明晃晃的,照得人睁不开眼。
“卫东,我不是在做梦吧?”秀-兰掐了自己胳膊一下,“嘶”的一声,疼得龇牙咧嘴。
“你掐我干嘛?”
“我看看是不是真的疼。”
我看着她那傻乎乎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。
笑着笑着,眼眶就湿了。
从下岗的绝望,到潘家园的嘲笑,再到此刻的柳暗花明。
这短短的几天,像过了一辈子那么长。
“秀兰,”我拉着她的手,“等拿到钱,咱们第一件事,就是去买个大房子。带暖气,带卫生间的那种。”
“嗯!”她重重地点头。
“再给你买好多好多漂亮衣服,金项链,金耳环!”
“嗯!”
“再给儿子请最好的家教,让他上最好的学校!”
“嗯!”
我们俩,就像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,站在大街上,畅想着未来。
那感觉,真好。
消息,很快就传开了。
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。
“听说了吗?机床厂那个下岗的林卫东,捡了个大漏!”
“什么漏啊?”
“一个破碗,据说是柴窑!拍卖行估价一百万!”
“真的假的?!”
“千真万确!人家拍卖行的专家都上门了!”
一时间,我成了整个大院,甚至整个厂区的焦点人物。
以前在路上碰到,假装看不见我的老同事,现在隔着老远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
“哟,卫东,气色不错啊!这是要发大财了!”
“卫-东,以后发达了,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伙计啊!”
就连我那个势利眼的小舅子,也提着两瓶好酒,颠儿颠儿地跑来了。
“姐夫,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!你这叫什么?真人不露相!”
他一边给我捶背,一边谄媚地笑着。
“姐夫,你看我那工作,天天累死累活的,也挣不了几个钱。要不,你给我投点资,我也做点小生意?”
我看着他那副嘴脸,心里一阵反胃。
想当初,我刚下岗的时候,去他家借钱,他是怎么说的?
他说:“姐夫,不是我不帮你。你看我这日子也紧巴巴的,实在是拿不出钱来。再说了,你一个大男人,手脚齐全的,干点什么不能挣钱?非得去借?”
现在,他倒是一口一个“姐夫”叫得亲热。
我没搭理他。
秀兰把他拉到一边,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
他走的时候,脸色很难看。
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。
在这短短的时间里,我算是看了个通透。
当然,也有真心为我高兴的。
比如范叔。
他把我叫到家里,千叮咛万嘱咐。
“卫东,树大招风。最近这段时间,你跟秀兰都低调点,别到处张扬。钱还没到手,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”
“还有,那些攀关系、借钱的,你都要留个心眼。人心隔肚皮,不得不防。”
我把他的话,都记在了心里。
拍卖会定在一个月后。
那一个月,是我人生中最难熬,也最甜蜜的一个月。
我和秀兰,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过。
我们不再去想下岗的事,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。
我们的生活,仿佛一下子就充满了阳光。
我们开始计划着拿到钱以后要做什么。
秀兰说,她想去一趟南方,看看电视里说的那种高楼大厦。
我说,我想开一个小小的古玩店,不为挣钱,就为自己那点念想。
儿子说,他想要一台电脑。
所有的梦想,都变得触手可及。
但同时,我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那个碗,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碗了。
它承载了我们全家的希望。
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。
梦见拍卖会上,那个碗被人以天价拍走,我跟秀兰在台下相拥而泣。
也梦见那个碗流拍了,所有人都用嘲笑的眼神看着我。
我变得患得患失。
秀兰看出了我的焦虑。
她安慰我说:“卫东,别想太多。就算……就算那碗卖不出去,也没什么。大不了,咱们还跟以前一样过日子。你去找个活儿干,我好好上班,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”
我知道,她是在安慰我。
可我怎么能不想呢?
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我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,除了向前,别无选择。
八
拍卖会那天,终于到了。
地点在京城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。
我和秀兰,是坐着拍卖行派来的小轿车去的。
那是我这辈子,第一次坐这么好的车。
车里有空调,座位软得像沙发。
秀兰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我穿着范叔特意借给我的一身体面的西装,虽然有些不合身,但人也精神了不少。
宴会厅里,金碧辉煌,衣香鬓影。
来参加拍卖会的,非富即贵。
男的西装革履,女的珠光宝气。
我们俩,混在人群里,就像两只不小心闯进天鹅湖的土鸭子,显得格格不入。
我看到了一些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面孔,有大企业家,有当红的明星。
他们谈笑风生,举止优雅。
而我,连走路都觉得手脚不协调。
“卫东,我……我有点害怕。”秀兰小声说。
“别怕,有我呢。”我握紧了她的手,故作镇定。
其实,我比她还紧张。
我的心脏,跳得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一样。
我们的座位,被安排在第一排。
这是陈专家特意安排的,方便我们看清楚拍卖的过程。
拍卖会开始了。
一件件拍品,被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端上台。
有字画,有玉器,有青铜器。
拍卖师在台上,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,介绍着每一件拍品。
台下的富豪们,云淡风轻地举着手里的号牌。
价格,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速度,疯狂地向上飙升。
几十万,几百万……
那些数字,对我来说,就像是天方夜谭。
我看得目瞪口呆。
原来,钱在这些人的眼里,真的就只是一个数字。
秀兰更是大气都不敢出,眼睛瞪得溜圆。
终于,轮到我的那个碗了。
当礼仪小姐,用戴着白手套的双手,小心翼翼地将它捧上台时,我的呼吸,瞬间停止了。
它被放在一个铺着红色丝绒的展台上,在聚光灯的照射下,散发着柔和而迷人的光晕。
那片雨过天青色,仿佛有了生命。
整个会场,都安静了下来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聚焦在了那个小小的,甚至有些残破的碗上。
“各位来宾,接下来这件拍品,是我们本次秋季大拍的压轴重器。”
拍卖师的声音,充满了激动。
“五代后周柴窑,天青釉撇口碗!”
“柴窑,位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,素有‘瓷皇’之称。其‘雨过天青云破处’的釉色,千百年来,引得无数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为之倾倒。”
“然,柴窑存世稀少,如凤毛麟角。完整的器物,更是闻所未闻。今天,我们有幸能见到这件虽然口有残,但神韵犹存的柴窑真品,实乃三生有幸!”
“这件拍品,是华夏文明的瑰宝,是陶瓷艺术的巅峰!它的价值,无法用金钱来衡量!”
“多余的话,我不再赘述。懂的人,自然懂。”
“此件柴窑天青釉撇口碗,起拍价,人民币一百万元!每次加价,不少于十万元!现在,开始竞拍!”
拍卖师的话音刚落。
台下,立马就有人举起了号牌。
“一百一十万!”
“一百二十万!”
“一百五十万!”
价格,瞬间就攀升了上去。
我跟秀兰,紧张得手心全是汗。
我们俩紧紧地握着手,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掌心的湿热。
举牌的人,越来越多。
有香港来的大富商,有台湾来的收藏家,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。
他们似乎都对这个碗,志在必得。
价格,很快就突破了二百万。
“二百五十万!”
“三百万!”
“三百五十万!”
每当拍卖师喊出一个新的价格,我的心,就跟着颤抖一下。
秀兰已经不敢看了,她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,身体微微发抖。
当价格喊到五百万的时候,场上的竞争,开始变得白热化。
只剩下三个人还在坚持。
一个是坐在前排的香港富商,一个是戴着眼镜的儒雅中年人,还有一个,是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神秘的白发老人。
“五百一十万!”香港富商举牌。
“五百二十万!”儒雅中年人紧随其后。
“六百万!”
那个白发老人,一开口,就直接加了八十万。
全场一片哗然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投向了那个角落。
香港富商和儒雅中年人,都皱起了眉头。
他们显然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加价,打乱了节奏。
拍卖师也愣了一下,随即更加兴奋起来。
“六百万!这位先生出价六百万!还有没有更高的?六百万一次!”
香港富商犹豫了一下,最终还是放下了号牌。
儒雅中年人,则跟旁边的人低声商量了几句,也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“六百万两次!”
拍卖师的声音,在空旷的宴会厅里回荡。
我的心,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六百万……最后一次!”
“铛!”
拍卖槌,重重地落下了。
“成交!”
“恭喜这位先生,以六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,拍得这件国之重宝!”
全场,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而我,却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我的脑子里,只有一个数字,在不停地盘旋。
六百万。
六百万。
我转过头,看着秀兰。
她也正抬起头,看着我。
她的眼睛里,噙满了泪水。
我也哭了。
眼泪,不受控制地,从眼角滑落。
这不是激动的泪,也不是喜悦的泪。
那是一种,五味杂陈的,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情绪。
有委屈,有辛酸,有如释重负,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我仿佛看到了我爸,他正站在云端,冲着我欣慰地微笑。
我仿佛看到了潘家园那个叫马三儿的摊主,他那张嘲讽的脸,在我的泪光中,变得模糊,然后破碎。
我紧紧地抱住秀兰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成功了。”
九
拍卖会结束后,陈专家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。
“林先生,林太太,恭喜二位!”
他脸上的笑容,比我们还要灿烂。
“按照合同,扣除百分之十的佣金,以及相关税费后,您最终可以拿到手的金额,是五百二十八万元。”
五百二十八万。
这个数字,从陈专家的嘴里说出来,轻飘飘的。
但落在我跟秀兰的耳朵里,却重如泰山。
我们俩,晕晕乎乎地办完了所有的手续。
走出酒店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
京城的夜,灯火璀璨。
我们没有坐拍卖行安排的车,而是选择了走路回家。
我们需要一点时间,来消化这个巨大的惊喜。
我们俩,手牵着手,走在长安街上。
谁也没有说话。
但彼此的心,却靠得很近。
走了很久,秀兰突然停下脚步。
“卫东,你说……我们以后该怎么花这笔钱啊?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摇了摇头,笑了,“慢慢想,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来想。”
回到家,儿子已经睡了。
我们俩,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看着那张存着五百多万巨款的银行卡,相对无言。
感觉,还是像在做梦。
第二天,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去银行,取了十万块钱现金。
我把那厚厚的一沓钱,放在了桌子上。
秀兰看着那堆钱,眼睛都直了。
“卫东,你取这么多钱干嘛?”
“去买房。”我说。
我们看中了亚运村附近的一个新楼盘。
三室一厅,一百二十平米,精装修,家电齐全。
在当时,那是全北京最好的房子。
我们几乎没有犹豫,就全款买了下来。
拿到新房钥匙的那天,秀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,又哭又笑。
她说:“卫东,我这辈子,做梦都没想到,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”
搬家那天,我们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。
包括那个曾经看不起我的小舅子。
他看着我们家那宽敞明亮的客厅,看着阳台上能俯瞰整个京城夜景的落地窗,眼睛都红了。
他端着酒杯,一个劲儿地给我敬酒,说的话,比蜜还甜。
我只是笑了笑,没有多说什么。
有些事,过去了,就让它过去吧。
生活,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秀兰辞掉了工作,当起了全职太太。
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,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-染。
她的脸上,重新绽放出了笑容。
儿子转到了全北京最好的中学。
我们给他买了电脑,请了家教。
他的成绩,突飞猛进。
而我,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我在琉璃厂,盘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,开了一家叫“拾遗斋”的古玩店。
我不指望它挣钱。
我只是想,能有一个地方,安放我的那点爱好。
我每天在店里,喝喝茶,看看书,跟南来北往的藏友聊聊天。
日子,过得悠闲而惬意。
我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,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
我终于,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有时候,我也会想起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下午。
想起潘家园的尘土飞扬,想起马三儿那张嘲讽的脸。
有一天,我心血来潮,又去了一趟潘家园。

那里,还是跟以前一样,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
我找到了马三儿的摊位。
他还是老样子,穿着那件蓝布褂子,正唾沫横飞地跟一个游客推销他的“宝贝”。
他看到我,愣了一下。
显然,他已经不记得我了。
也是,对于他来说,我只不过是他坑过的无数“棒槌”中的一个,无足轻重。
我走到他的摊位前,蹲下身子,假装看东西。
“嘿,哥们儿。”他凑了过来,还是那副油滑的腔调,“看上嘛了?我这儿的东西,保真!”
我笑了笑,指着一个跟他当年卖给我那个碗差不多的破碗。
“这个,怎么卖?”
他撇了撇嘴,一脸不屑。
“那玩意儿?破烂一个。你要是喜欢,十块钱拿走。”
我看着他,突然觉得有些可怜。
他永远也不会知道,他曾经亲手,把一个价值六百万的宝贝,当成一个破烂,卖给了我。
他错过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机会。
不是因为他眼力不行。
而是因为,他的心里,只有钱,只有算计。
他看不到那些老物件背后,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。
他也感受不到,那种与国宝失之交臂的,刻骨铭心的遗憾。
我站起身,没有再说什么,转身离开了。
走出潘家园的时候,夕阳正红。
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喧嚣的市场。
我知道,属于我的那个传奇,已经结束了。
但生活,才刚刚开始。
我的人生,因为那个破碗,而彻底改变。
但我也知道,真正改变我的,不是那六百万。
而是,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,我没有放弃自己的那份热爱和坚持。
是那份坚持,让我在绝望中,看到了一丝光。
也是那份热爱,让我在无数的嘲笑和质疑声中,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人生,就像一场寻宝。
有时候,最珍贵的宝贝,不是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。
而是我们那颗,永远相信梦想,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,勇敢的心。